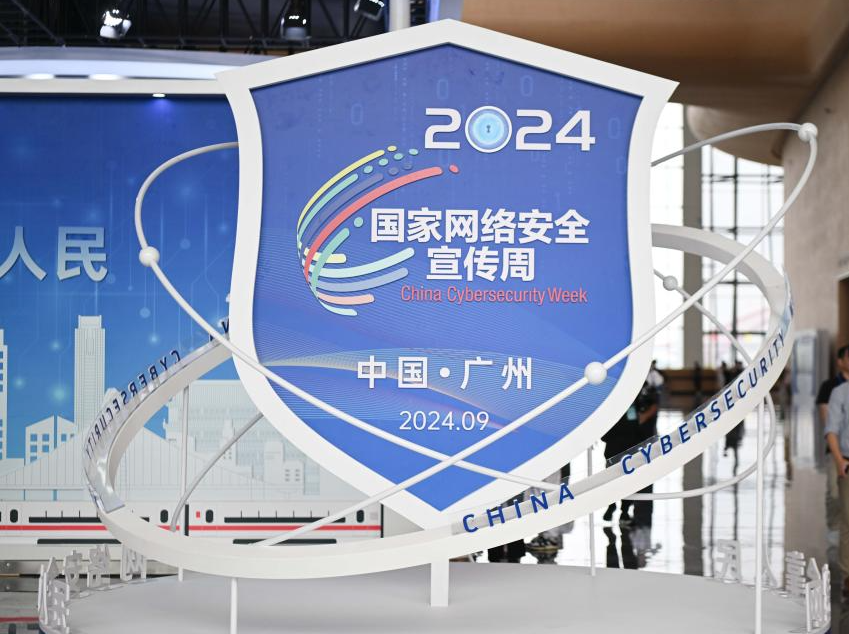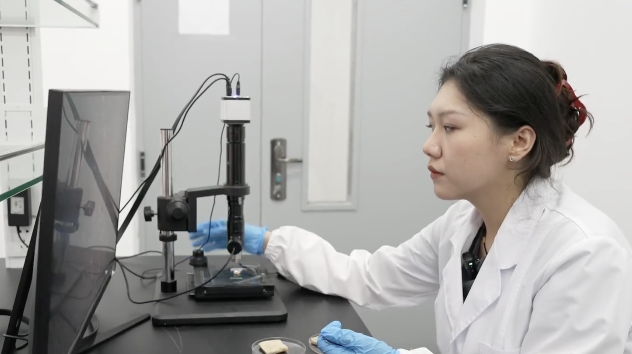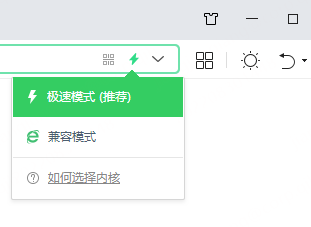科技日報記者 陳瑜 都芃
吞下一顆小小的尿素膠囊,半個小時后,對準集氣袋長呼一口氣,等待片刻,是否感染幽門螺旋桿菌便一目了然。這種檢測方法無痛、無創、快速、簡便,已成為幽門螺旋桿菌檢驗的“金標準”。
該檢驗背后,一種名叫碳-14的放射性同位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長期以來,我國碳-14嚴重依賴進口,全球僅有少數國家掌握碳-14量產技術。
“為填補這項空白,中核集團秦山核電組建研發團隊矢志攻關,歷時5年多,在全球首次實現應用商用重水堆機組批量生產碳-14。”秦山核電總經理尚憲和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日前,首批產品從秦山核電基地正式發運投放市場,標志著我國碳-14實現從自主研發、自主生產到市場化供應全產業鏈貫通。
自主計算中子能量
我們的生活與“碳”密切相關。在自然界中,作為碳元素的同位素之一,碳-14占比微乎其微,卻用途廣泛。
自2010年起,碳-14市場出現缺口,6年間價格上漲5—10倍,需求仍與日俱增。
要實現大規模供應,只有依賴人工生產,采用反應堆進行輻照是目前最主要的生產手段。由于生產周期長、產量少,國內大部分碳-14來自國外,供應常常會被“卡脖子”。
自2019年起,秦山核電探索利用商用重水堆核電機組批量生產碳-14。
借助反應堆生產碳-14,需要發生中子輻照俘獲后釋放質子(n,p)反應。秦山核電所屬浙江秦山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孟智良將晦澀難懂的反應過程比作打臺球:一個中子與一個含有7個質子、7個中子的氮-14原子核發生“碰撞”,中子被氮-14原子核吸收,然后“彈”出一個質子。這時候,氮-14就變身具有8個中子和6個質子的碳-14了。
要實現(n,p)反應,中子能量必須達到一定的閾值。
從理論上講,重水堆的中子密度高,在相同輻照時間下,更容易發生核反應,可以生產更多碳-14。
然而,重水堆中子雖多,但都是能量較低的熱中子,距離閾值要求相差甚遠。這種低能量的中子能否引發(n,p)反應,大家看法不一。為了尋找答案,研發團隊一頭扎進浩如煙海的文獻堆里。
秦山核電的兩臺重水堆為國外引進的堆型,以“交鑰匙”的方式建設,試驗數據、分析模型以及同位素生產等關鍵信息都是“黑匣子”。信息碎如星光,團隊成員化身信息拼圖大師,一點點拼湊與碳-14生產沾邊的研究報告和技術檔案。
“數月時間轉瞬即逝,大家精力已快耗盡,關鍵的中子能量數據卻依舊躲在重重迷霧之中。”孟智良回憶,無路可退時,團隊下定決心,“自己算!”
沒有現成的模型,就自己搭建。建模不易,驗證更難。他們唯一能依靠的參照物,是文獻中的數據。每一個模型參數都需要經過數據的反復“拷問”和校準。經歷十余輪計算、比對、分析、調整、再計算后,他們最終確定了可靠的模型。
當呈現在屏幕上的計算結果清晰顯示熱中子可以引發反應時,大家終于長吁一口氣:從原理上講,在商用重水堆生產碳-14完全可行!
獨立開發分析方法
確認原理可行后,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擺在項目團隊面前:碳-14靶件入堆后,如何保證反應堆安全?
重水堆是一個非常精密復雜的系統,每一項設計都經過嚴格論證。
“如果將堆芯比作筆筒,堆芯中的燃料棒就像一支支筆。”秦山核電專項工程處項目支持科副科長樊申打了個形象的比方,“為確保反應堆安全穩定運行,筆的擺放位置都是經過嚴格計算的。”
將碳-14靶件這支新“筆”插進“筆筒”后,會不會給反應堆運行帶來擾動?
要打消疑慮,必須反復論證。
受制于種種因素,聯系外方開展分析計算并不現實。面對困難,項目團隊只能再次下決心——自己干!
他們從消化以往的計算報告開始,自行開展安全分析評價,核心就是評估靶件入堆及輻照對堆芯停堆參數的影響。
“經過一周左右的頭腦風暴,我們梳理出8種基本堆芯狀況。在此基礎上,再對每種基本堆芯狀況進行小變動的影響分析。”樊申說,每種基本堆芯狀態要開展的小變動計算多達700多種,并且每次計算都涉及物理和熱工耦合,難度極大。
在始終燈火通明的機房內,團隊按期完成了近6000種工況的計算模擬,積累了大量試驗數據。接下來,大家又馬不停蹄地對過往的計算報告進行還原與復現,逐個工況、逐個數據比對有無靶件情況下,各項安全控制參數是否對得上。
周而復始的計算模擬、數據比對……直至每一種工況都符合安全要求。奮戰6個多月后,論證終于迎來收官階段。依托充分的工況模擬、翔實的數據分析,經過反復論證,團隊證明了靶件入堆后安全可靠。
創新建立驗證體系
原理可行,安全有保證,研制碳-14靶件成為最后一塊“硬骨頭”。
“靶件入堆后,要經歷長時間的輻照,一旦破裂,其內部的輻照材料就會散入堆芯,形成異物風險。”孟智良說,因此靶件研制必須通盤考慮制造、輻照安全以及后端處理便利性等因素。
要生產靶件,首先要解決原材料問題。
研發團隊聯合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開展工程設計和靶件研制,并向從事過碳-14生產的單位進行專題咨詢,最終確定了以氮化鋁粉末作為靶材、以鋯合金作為包殼的靶件設計方案。
該方案對雜質含量等指標控制極為嚴格,甚至個別參數根本沒有經過驗證的檢測方法,這里面就包括化學性質活潑的游離鋁。
團隊似乎遇到了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
怎么辦?他們沒有氣餒,沒有現成的檢測方法,就從基本原理出發,從零開始想辦法。
一個寂靜的深夜,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會議室氣氛近乎凝固之際,角落里的一個聲音打破僵局:“我們是否可以通過置換法,將游離態鋁轉變為離子態鋁,然后再使用質譜法進行檢測。”
這個想法瞬間激起所有人的靈感。
經過幾輪頭腦風暴,大家認為,這條路雖然艱難,但一定可行。此時,另外一個問題被擺到桌面——作為置換材料的鹽類物質家族成員浩繁,誰最合適?
在暫時無法通過理論找到明路時,就嘗試用“笨辦法”來“大海撈針”。大家沒有猶豫,說干就干。經過反復排列、組合、嘗試、比較、排除,一款性能優異的置換鹽從萬千候選者中脫穎而出。
緊接著,團隊又先后破解其他雜質元素的檢測難題,曾經橫亙在精確檢測路上的“攔路虎”被一一掃清!靶件順利面世,碳-14批量生產的最后一個環節被打通。
目前,碳-14被廣泛應用于考古、農業、化學、醫學和生物學等領域。
“秦山核電的碳-14產能可充分滿足國內需求,將有力帶動我國同位素應用產業鏈集聚發展。”尚憲和告訴記者,“下一步,我們將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以同位素產業為支點,全力撬動千億級核技術應用市場。”
(科技日報記者張蓋倫、代小佩對此文亦有貢獻)